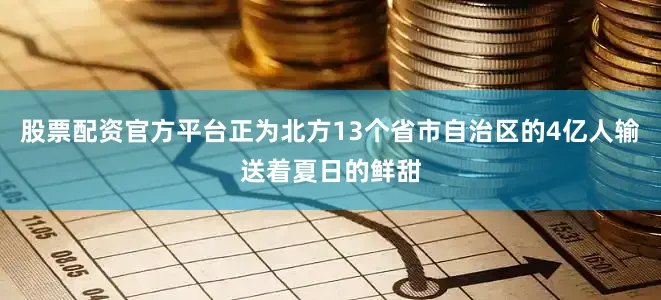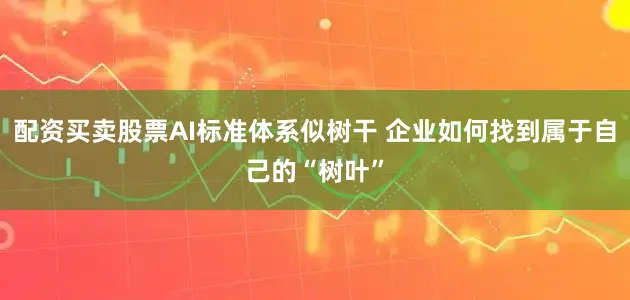1940年初,蒋经国在与私人秘书余致浚讨论抗战的最新捷报时,突然提到了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。他主动表达了对这篇军事理论文章的钦佩之情,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感受。蒋经国说道:“这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,清晰地划分了战争的各个阶段,分析了战争形式的转变,并深入探讨了战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挑战。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洞察力非常深刻,文章的预见性和说服力令人信服。” 这些评价充分体现了蒋经国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高度认可。
图注:毛泽东在抗大讲解《论持久战》的场景,摄于1938年,由徐肖冰拍摄。
在那时的中国,抗日战争刚刚开始,国内弥漫着两种极端的声音:一种是“速败论”,主张中国必然会因国力和军事实力差距而快速失败,宣扬亡国论,认为抵抗无望;另一种则是“速胜论”,认为只要集中力量、进行一两次决定性的战役(如台儿庄战役),便可轻松击败日本。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日本的强大和中国的弱小。随着台儿庄战役等一次次的失败,速胜论逐渐转向了速败论。
展开剩余74%在中国抗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艰难时刻,尽管战局依旧严峻,国内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思想上都充满了混乱,许多投降派的声音不绝于耳。就在这种时候,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仅用不到十天的时间,便完成了5万字的军事理论巨著《论持久战》。这一作品一经发表,便在党内迅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。陈云感到毛泽东的观点深刻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,认为这对全党和全国抗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不久后,陈云建议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干部中讲解。毛泽东接受了这一建议,开始在延安的抗大等学校和各党政机关进行讲解,并将《论持久战》印刷成油印版,广泛发放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知名人士,都对这部作品表现出了极高的评价。
1938年11月25日,蒋中正于湖南衡山召开“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”,商讨联合抗日事宜。会议中除了有众多的高级军官参加,还包括了八路军代表周和叶。周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《论持久战》的基本思想,白崇禧也在听后表示:“毛先生的大作自今年5月问世以来,我已经反复阅读,并向委员长做了诚恳推荐。我总结毛先生的理论,就是‘以空间换时间,积小胜为大胜’。” 不久后,《论持久战》与蒋中正的讲话一起,传发至各位高级将领手中,包括那些未能亲临会议的人。
宋庆龄在收到《论持久战》后,立刻将其翻译成英文,并通过国际渠道发布,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。美国驻中国战区的司令史迪威将军在阅读过《论持久战》后,称这本书是“绝妙的教科书”,并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快对中国的援助,特别是在武器装备上的支持,认为这会加速中国的胜利。
土木系的陈诚最初对《论持久战》并不以为然,但当武汉、长沙相继沦陷后,他再次翻阅此书,并在其中批注了许多战例。陈诚还专门请周和学员们讲解《论持久战》和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备问题》。如今,陈诚批注过的《论持久战》仍被珍藏在台北的私人图书馆中。
《论持久战》凭借其高远的战略眼光,成功预测了抗日战争的三大阶段,甚至连蒋经国也曾自述阅读此书七、八遍,深受启发。
蒋经国的私人秘书余致浚,他自己却是一位地下党员。当时,他负责起草蒋经国的发言稿,没想到在一次谈话中,蒋经国提到《论持久战》时,流露出了对毛泽东的极大钦佩。余致浚在一份材料中提到,1940年年初的一个傍晚,蒋经国因听到抗日战线传来喜讯而心情愉悦,便找余致浚和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聊起了前线的胜利消息。正当大家谈兴正浓时,蒋经国突然转移话题,提到了《论持久战》。余致浚记得,他从未与蒋经国谈论过中共领导层的事情,但蒋经国这次主动提起毛泽东的文章,显然非常感兴趣。蒋经国称,这篇文章不仅深刻分析了抗战的形势、战争各阶段的演变,还精准预测了战争中的困难与问题,读后令人深感信服。蒋经国表示,他已翻阅《论持久战》七八遍,甚至在书上做了许多标记,书页已经翻得破旧不堪,旁边的文字有中文也有俄文,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重视和喜爱。
这些细节再次表明,《论持久战》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,也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和战略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发布于:天津市配资app,配资网首页官网,最新股票配资平台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